
世聯會保育場幫忙記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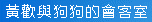

首先要先謝謝笨笨於 1月24日一起到世聯會保育場幫忙。一行四人(全是娘子軍)遠征到淡水小北投已近中午時分,飯也沒吃就開始分工合作。我們抵達前已有三位義工前去幫狗洗澡。洗好澡的狗由世聯會義工黃小姐負責打針(治療皮膚病的,非預防針是),我負責抓狗並安撫狗的情緒,以及幫已打針的狗頸部繫上布條以示區別。
皮膚病的狗真是多,極度嚴重全身無毛有,腸炎的也有。壯大如羅威拿、瘦弱如貴賓犬、老弱殘障全部混在一起。我想監獄電影裡強者欺壓弱小的情節隨時在此上演。生存是殘酷的。
保育場有兩位常駐工作人員,一位約五十來歲,據說原為遊民,因為愛狗受雇於此,脾氣溫和從不打狗。另一位是七十三高齡,湖北人的退役老伯伯,之前一直是他獨自管理狗舍,試想二、三百隻狗耶,吃喝拉屎吵鬧打架,每天都要面對,我只是呆一天就快虛脫。
老伯伯除了照顧保育場的狗,也餵食附近山區的流浪狗。附近有一座高爾夫球場,球場的人恨狗會拿球桿打狗。
黃昏時,伯伯開車送我們下山,就延著山路放置食物。有一處隱密的山間小路藏匿著十來隻流浪狗,狗要天黑以後才會出現,所以伯伯也無法親近牠們。他細心的在那兒用木板架起簡陋小小屋,將一部份飼料置於小屋內以防下雨不會淋濕,除此還放有幾個裝水的容器。
放好飼料後發現有一具已成白骨的狗屍,形狀完整成側臥的姿態,我既驚駭又心疼的脫口而出:『怎會這樣?可憐的孩子!』
『不會不會,最痛苦的時候已經過去了。』同行的水瓶女子輕聲說,眼裡有淚光…
保育場搭有一簡單的鐵皮屋供老伯伯住,五、六坪大。雖有冷氣但太陽西晒時異常悶熱,尤其夏季時節。七十三歲的老人家,雖然瘦,身子骨看起來還算硬朗,腦筋清楚,待人很和善。伯伯長久以來就有暈眩的老毛病,本來只是一年一兩次,最近常發病,晚上又睡不好,狗吠聲擾人安睡。
老人到世聯會之前曾做過大樓管理員,在台已無親人,本身亦養有十來隻流浪狗。屋內有數隻狗與老人共處一室,其中一隻是雙眼全盲的北京狗。
我注意到伯伯常常在大腿等處搔抓,他說可能是長期與狗親暱共處被感染。不知怎的,回家我老想著這事,猜想老人家很可能是冬季癢,皮膚油脂不夠,缺乏維生素B群,下次去記得幫他帶一瓶嬰兒油或甚麼的和維他命。
這個老人家改變了我對老竽阿的感覺。